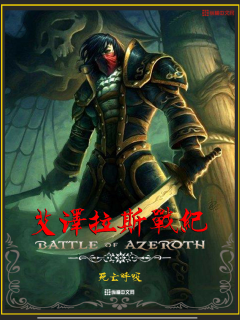阿比盖尔·巴罗夫。
我曾经的记忆里其实没有这个名字,即便是现在我对这个名字的了解也并不多。虽然我跟这个人确实接触过。
可你也别忘了,他是奥特兰克人,可奥特兰克亡国了,后来他们家投靠洛丹伦,然后洛丹伦王国也亡国了。
王国亡国,亡的不光是国,还有这个国的文化和历史,以及有可能的一切。
所以……
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当知道要去巴罗夫家的时候我还是蛮兴奋的,不光可以出去玩,见天地,见众生,而且我越发感觉加入到他们的游戏中能体会到做别的事绝对体会不到的乐趣。
上层人的生活绝对不是一般人能窥探的。而我有条件可以窥探。
回住所的路上,一个穿着棕色衣服的精瘦细小毫不起眼的家伙从我身边经过一句话飘然而至。“孤狼有信,跟我来。”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往前走了不远转身进了一个小巷子。
跟他进了巷子,却发现还有一个家伙。我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那人赶紧摆手,“不用紧张,比尔。”他露出了他的戒指。“我是塔伦米尔的联络人。我叫埃布尔,他叫科尔。”他指了指旁边的家伙。
打量了一下这个叫埃布尔的三十多岁男人,“什么事。”
“孤狼想知道你最近怎么样了,你最近失去了联系。”他说。
“我在王储这找了个工作。”我说。“他不知道么?”
他的眼睛收缩了一下,“请牢记你的身份,比尔。”
“哼……”我瞥了那家伙一眼,“还有别的事么?”
“现在王储什么情况。”他问。
“他要去凯尔达隆……找巴罗夫。”面前的男人一本正经。
“什么时候。”
“后天。”
埃布尔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后点了点头,“那今晚你要有事做了。”
“做什么?”
“晚上六点,绿蘑菇酒馆左边的巷子,第二个拐角往右走进去,你去那等你。”他看了我一眼后转身走了。
晚上真的能做好多事,尤其适合做一些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事,非常的应时应景。
天刚刚擦黑我便提前到了那个地点,只不过我不喜欢走到巷子里面。
巷子里出现了一个人但随后他就躲到阴影里。躲在房顶的我把下面看得一清二楚。
我从屋顶摸过去瞅准刚才那人位置,直接从天而降将那人踹翻倒在地,匕首也顶在了他的脖子上。
“你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竟是埃布尔,他别过头来看着我。
“以防万一。”我伸手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时间刚刚好。”埃布尔穿了一身夜行衣。“走吧!”
穿过曲折小巷,行到尽头时看到了更远处的一座不是很大的独立别墅。
“这是哪?”我问。
“你没做功课么?”他略显惊讶地瞥了我一眼。
“我才来几天?”
“你真把自己当成护卫了?”他的眼神叫我心里不舒服。
“那又怎样?”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话。
“那今晚做什么你总可以告诉我吗?”
“你掩护我,我去做。”他不再看我。
现在是晚餐时间,住别墅的大概不是普通平民,最少也得是个商人,而且住这种规模的别墅小商人的财力是住不起的。我想说的是这个他们用晚餐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摸进了别墅里,准确地说是寝室。
这寝室很大,可里面装饰却并不华丽。
“找什么?”我压低了声音。
“找找笔记和书信。”
“就这样?”
“如果发现是与弗莱德•匹瑞诺德的信件,单独交给我。”
“与其他人的呢?”
“先找到再说。”
“你怎么知道会有与弗莱德的信件?”
“我不知道。”他说。
“那你让我找?”
“万一有呢?”
白了他一眼,“这是谁的家?”
“快点找。”他动作相当麻利。
没有那么多神奇暗格也没有什么机关,他的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找到了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堆书信。
埃布尔飞快地挑拣着书信,我好奇地打开了一封,没发现有什么异样的内容,也不反动。
“有什么发现么?”我把信递了过去。
“当然有。”他接过我手里的信件,把他手里的信递给我。
“这封有什么问题么?”我非常快速地浏览了一遍,而且里面似乎除了抱怨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这封信是史沫特莱•马伦男爵的书信,他可是个很有钱的家伙。”
“那有什么关系。”
“他太有钱了。”埃布尔将信拽了回去,然后把信都揣进了怀里。“这就是关系。”
“完活了?”
“走。”他转身就走。
“你要都揣走何必叫我找跟弗莱德的信,脱裤子放屁。”
“别废话,走。”他走向了阳台。
“这有好多珠宝呢。”我翻开了另一个箱子。
“我们不是贼。”埃布尔轻轻地推开阳台上的门走了出去。
“你这么高尚的么?”我把箱子放回了原处。“你还没告诉我这是谁家……”
你脸上的表情让我猜到你想说什么了。你是个聪明的家伙,有不少家伙现在还一脸懵呢。你是不是疑惑为什么我信都拿到了还不知道这是谁家?
确实不知道,这些信最前面的称呼没有名字,有些后面有落款,有些最后面没有。这种信整得跟留言条似的。
这时你只要不是个砂哔你或许就会问了,那怎么分辨是谁的来信?这就不得不说接下来要做的事了。
“偷什么?”我有些诧异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不是我没听见而是不敢相信,甚至很是怀疑。偷信无非是找证据找线索找把柄找小辫子,而现在他要去偷印章。
印章啊!
印章就是徽记,徽记是一个家族的专用符号或者标志。几乎所有的家族都用自己家族的徽记做印章,这种特殊标记用在信件和文件上面来显示权威性。我觉得我说明白了。
“偷那玩意干啥?”其实我能猜到是干啥,可不敢确定。
“我只负责通知你,然后带你去,让你配合我,至于给你解释问题,尤其是这个问题,并不在我的职责中也不在我的任务里。”他斜着眼看我。
“不说就不说么,啰里八嗦说这么多。”我白了他一眼。
“你这种菜鸟行为会害了你。”他说:“希望到时候别连累我们,更别牵扯到上面。”
“看把你心给操的,还牵扯到上面,你是个什么大人物么?”
他摇了摇头扭过头去。
“那东西在哪?”
他望着我们刚出跑出来的别墅没说话。
“你能一次性把活干完么?”我说。
“临时起意。”他说。
“你想干什么?”
“别废话,走吧。”他又走向了别墅。
“那玩意在刚才卧室里么?”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你叫我去?”我皱眉,“那个玩意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是萝卜刻的还是土豆雕的?”
“闭嘴,菜鸟。”
“你在开玩笑。”
埃布尔没理我。
“你叫我去偷这玩意,你干什么。”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扯特么淡……”我不是不满,是怀疑。
再次潜入宅邸,埃布尔说这人今晚可能不会回去住,所以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搜。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进了卧房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知道他的印章究竟什么样。书桌被我翻了个遍,没有丝毫发现。
其实我心里差不多知道那玩意什么样子,但它究竟是个戒指还是个别的什么玩意就不清楚了。所以把他卧房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可以做印章或者像印章的玩意。要是戒指的话那极大概率不在这里。
认真翻遍了他的珠宝箱后我发现了一个荣誉勋章,但这玩意太大,得有半个巴掌大小。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他书架上的书和柜子里的笔记日记。在看到他的一本牛皮封面日记本上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印章印迹后,抚摸着印迹上复杂的花纹我回忆着见过的所有跟这花纹有关的记忆。
这大概就是他徽记印章的样子,我猜的。可总不能给他把这玩意抠下来就留下个本,这太蠢了,所以直接揣走了那个本。
埃布尔在桌子上埋头写着什么。“没找到,就找到一个笔记本。”
他没理我,过了好一会他才放下了笔,拿起那张纸轻轻地吹着上面的墨迹。“既然没找到看来就在他身上了。”
“应该是。”我附和道。“你写的什么?”
“一封信。”
“在这里写信?”我想看看信上写的是啥。
“别废话。”他轻轻吹着。
“那接下来呢?”
“再去偷。”
“那得等到今晚他睡,我都来这两次了!”我说。
“不会有第三次了,今晚他不回家。”他看着我说:“今晚是周五,他会在妓院过夜。”
一听妓院我来精神了。“这家伙精力这么旺盛的么?”
埃布尔将信仔细折好,放进了自己的怀中。
来到一家酒馆,酒馆门口几个丰腴的女子站在门口跟人插科打诨。
“你还没告诉我咱们偷的谁。”
埃布尔看一眼门口那几个流氓转身进了旁边的巷子。
“这家妓院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档啊。”我说。“那人这么有钱就来这种破地方?”
可转到酒馆后面才发现这家酒馆并不是个破地方,后面别有洞天。前面是酒馆,但是酒馆的背身则有很长的一段延伸出来的建筑,再往后还有一个连接的建筑。看着最后面这座有点高的四层小楼,我心里盘算着真要是在这里胡搞倒也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当我挂在屋外的窗户边往里看去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背对着我的一个白花花的大屁股和翘起来的两条腿,一个肥胖的跟猪一样的玩意正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奋力拼搏。
这场面对我而言还是过于刺激。
看着他俩翻来覆去换了好几个姿势,我还真就挺佩服这猪一样的家伙,别看头发都白了,胖成这个猪样,折腾这么一会也算好体力了。比小白脸强。
此时忽然闻到了屋里飘出来的一股很奇怪的香味,我赶紧往下爬了爬避开这个味道,两人结束后就开始聊天,这种等待简直就是煎熬,这比偷听王储那晚更叫我心焦。
屋里这对狂蜂浪蝶又吃又喝过了好一会才没了动静,此时我的胳膊已经有点发麻。
当从窗外往里看了看那俩人确实睡着了,我才从窗外钻了进去并打开了上锁的屋门把门外的埃布尔放了进来。
埃布尔并不言语,只用眼神示意我干活。
幽灵是不易察觉的,幽灵是没有心跳和呼吸的,幽灵走路比猫还轻,站到了床边的阴影中我就这样盯着床上这两位,这两条白花花的肉体就像宰完之后刮干净的猪。
窗外的月光并不明亮,但此时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仔细打量了下这个熟睡的家伙,忽然想起了这张脸。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不远处的埃布尔,他正盯着我看。
这老家伙行啊!这把子年纪了还能这样搞也是真不容易,这是吃了药啊还是用了什么魔法?看他肚子大成这个猪样,他低头都看不见尿尿的玩意,哎呦,那……都挛缩成啥了还能这么猛的?
俯下身子去看他手上戴着的戒指时,女人身上散发的独特香味让我身体竟然有了反应。这时候产生生理反应真不是我闲的,我也没这么如饥似渴成那样。
这香味不正常!
在朦胧的月光中,女人的身体分外娇嫩,月光刚好打在她身上,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肤如凝脂,那皮肤在月光下白的发亮。皮肤上面的绒毛都清晰可见。这女孩睡着之后五官也没有睡散了架,还是挺好看的,看年纪估计只有二十出头。那屁股,那小腰!极品!
这老东西挺他妈会享受。
我向埃布尔摇了摇头。埃布尔白了我一眼。
然后他开始翻他的衣服,他也对我摇了摇头。
这玩意这么难找的?
我摸到他衣服身边,仔仔细细地摸每一个边角,直到在他上衣外套的胸前摸到了那个插着羽毛的胸针。
说是胸针吧,确实是个胸针,但是这个胸针圆形底座略厚。取了下来摸了摸,我从怀里掏出了日记本。
对着月光,我将胸针扣在了日记本的印记上,我又仔细比对了下胸针和日记本上的印痕。一模一样。
我抬起头给埃布尔一个眼神,他撇了撇嘴拿着这个玩意闪出门去。
这个玩意要是被带走了,明天估计全城都得翻了天。我赶忙追了上去。
“你疯了!”轻轻关上门我压低了声音。
他也不搭茬,而是从怀里掏出了蜡烛和封蜡还有一个油布包。
“你要做什么?”看着他点燃了一根蜡烛,红色的封蜡在蜡烛的炙烤下融化了,滴滴答答地滴到他放在桌上的信封上。然后他将印章在油布包上按压了一下,又抬手将印章狠狠按到了封蜡上。
他拿起信对着封印吹了吹,说:“擦干净,给它放回去。”
我拿起桌上的胸针,他则自顾自着吹着封蜡。见我不动他压低了声音说:“擦干净,赶紧放回去,我在下面等你。”
“你想干什么?”紧跟他在黑暗的巷子里我忍不住问。
“或许是必要的工作。”他说。
“什么叫或许?哪有或许的必要的工作?”
“以后会知道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了,明天跟王储出去你最好注意安全。”
看着这家伙的眼睛,真不知道这是祝福还是忠告。